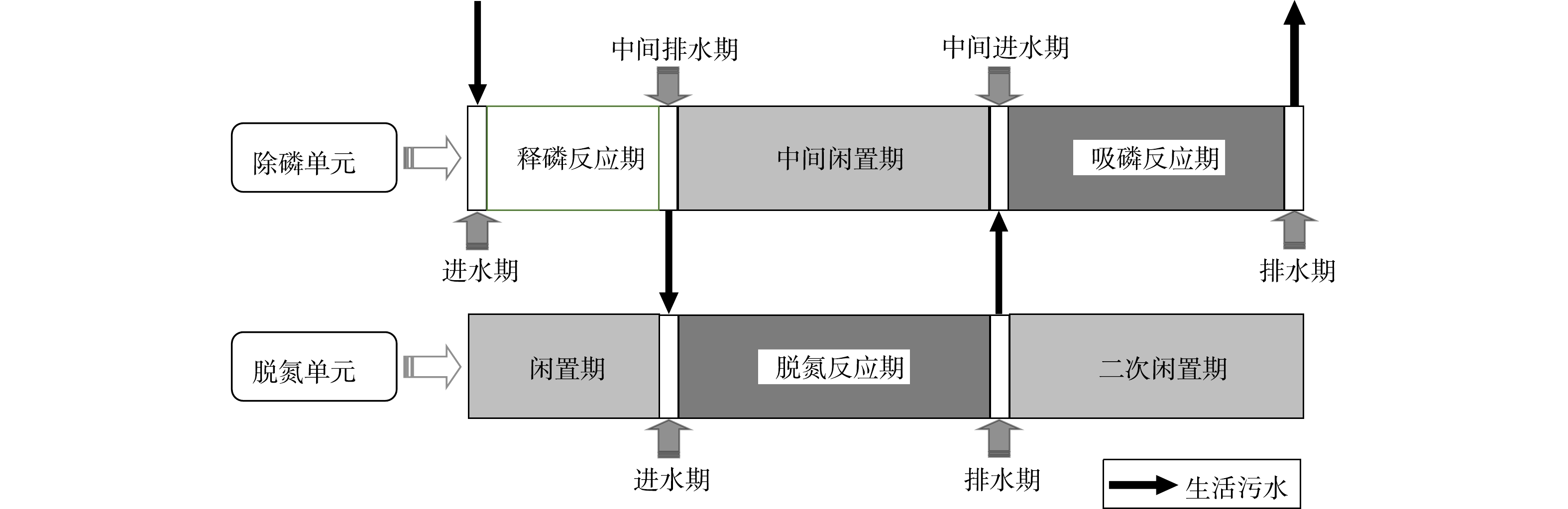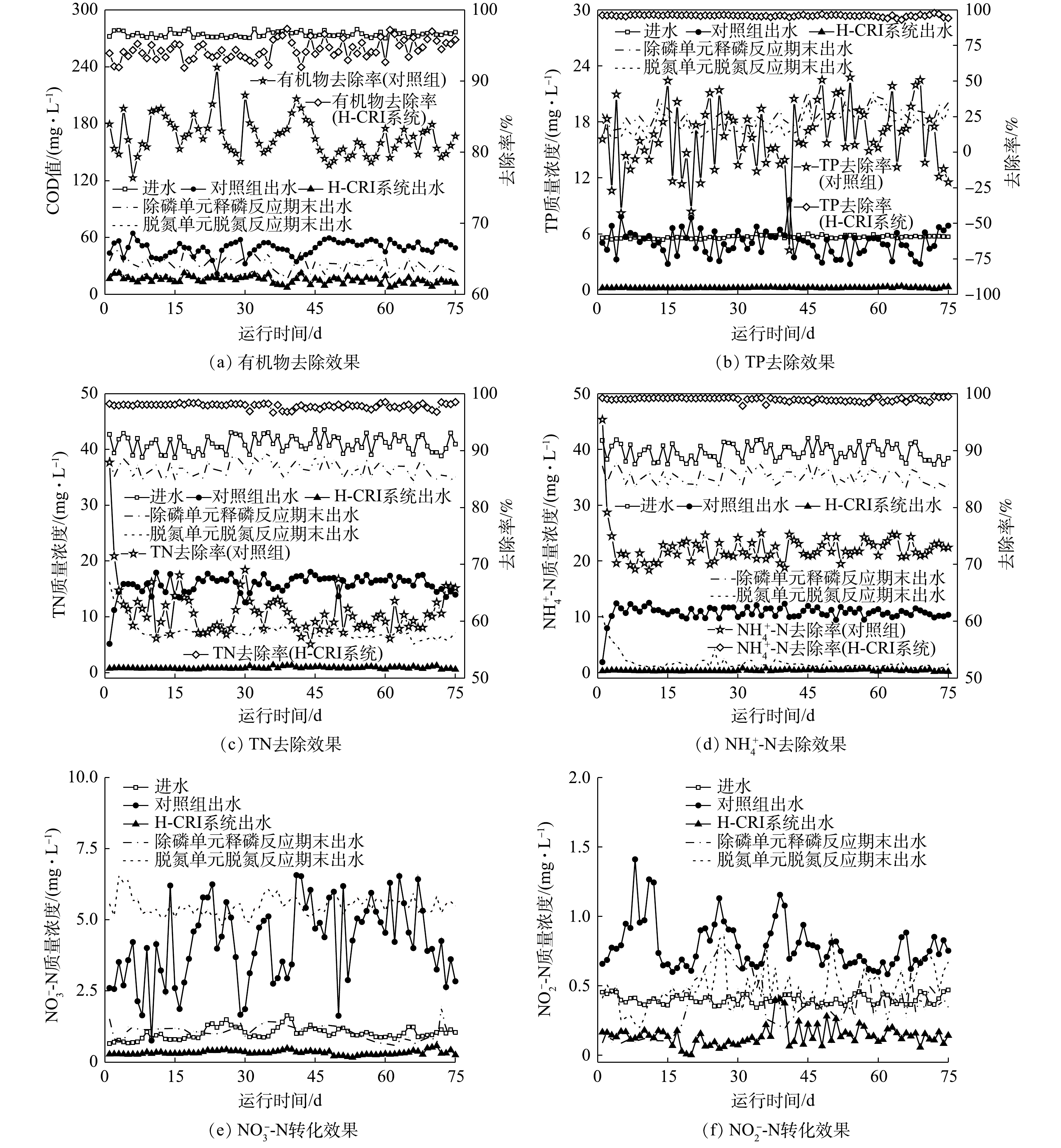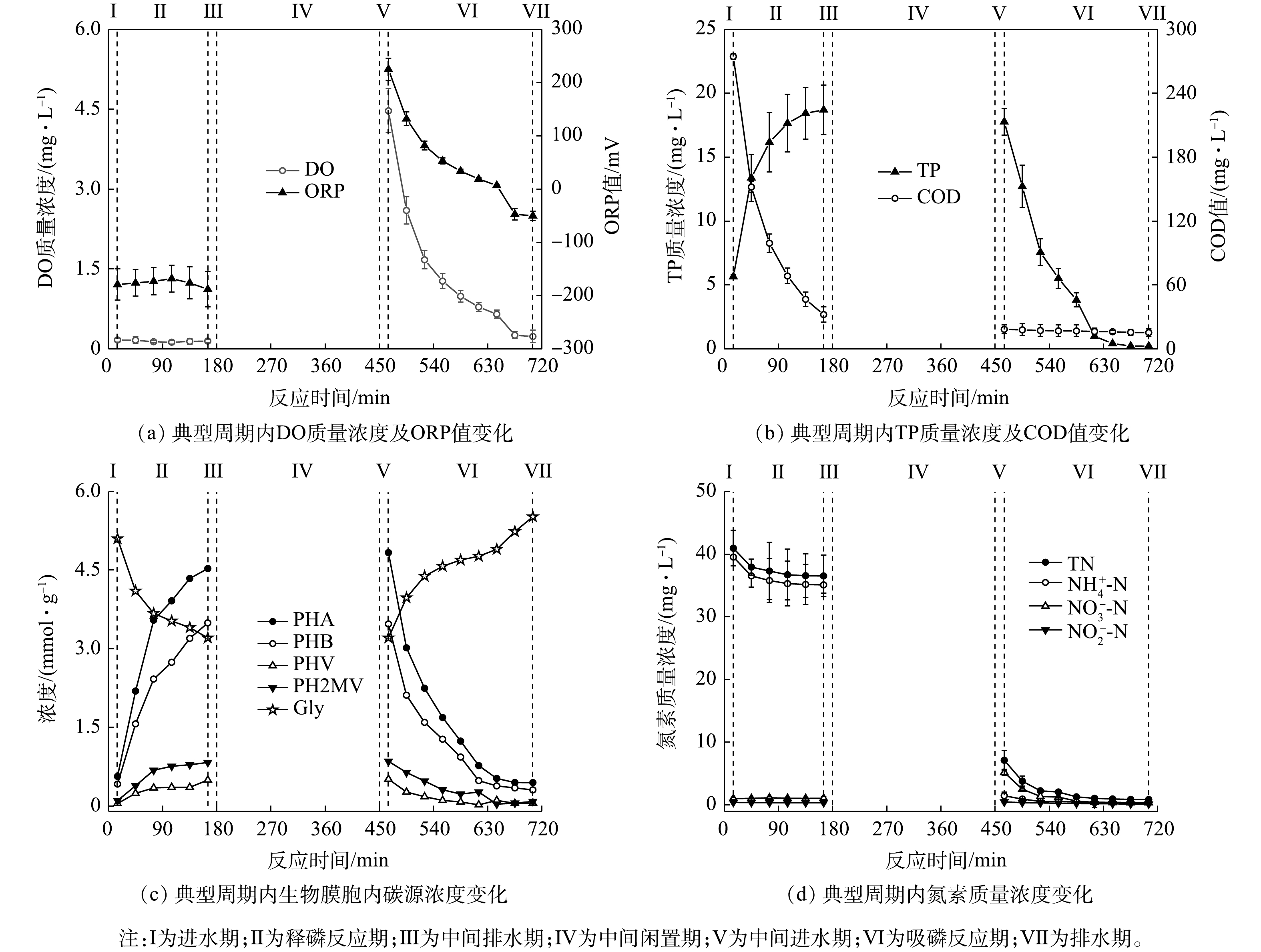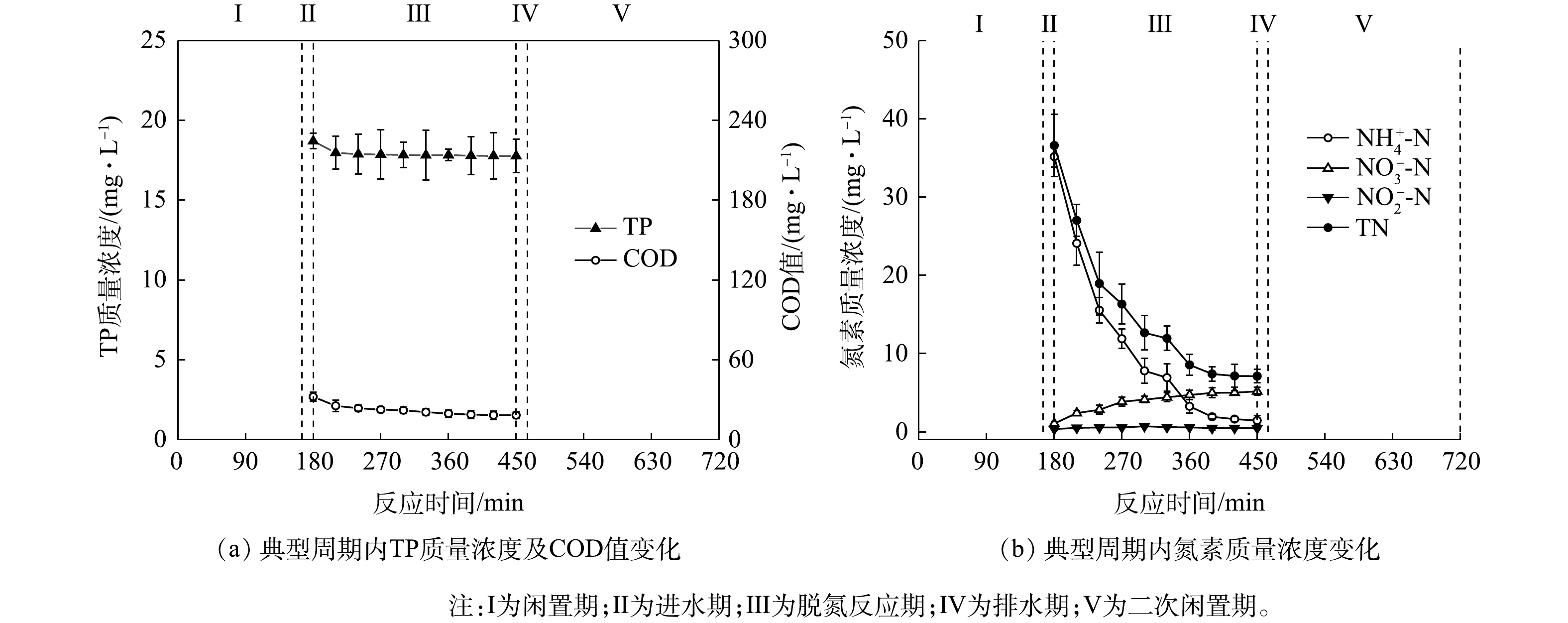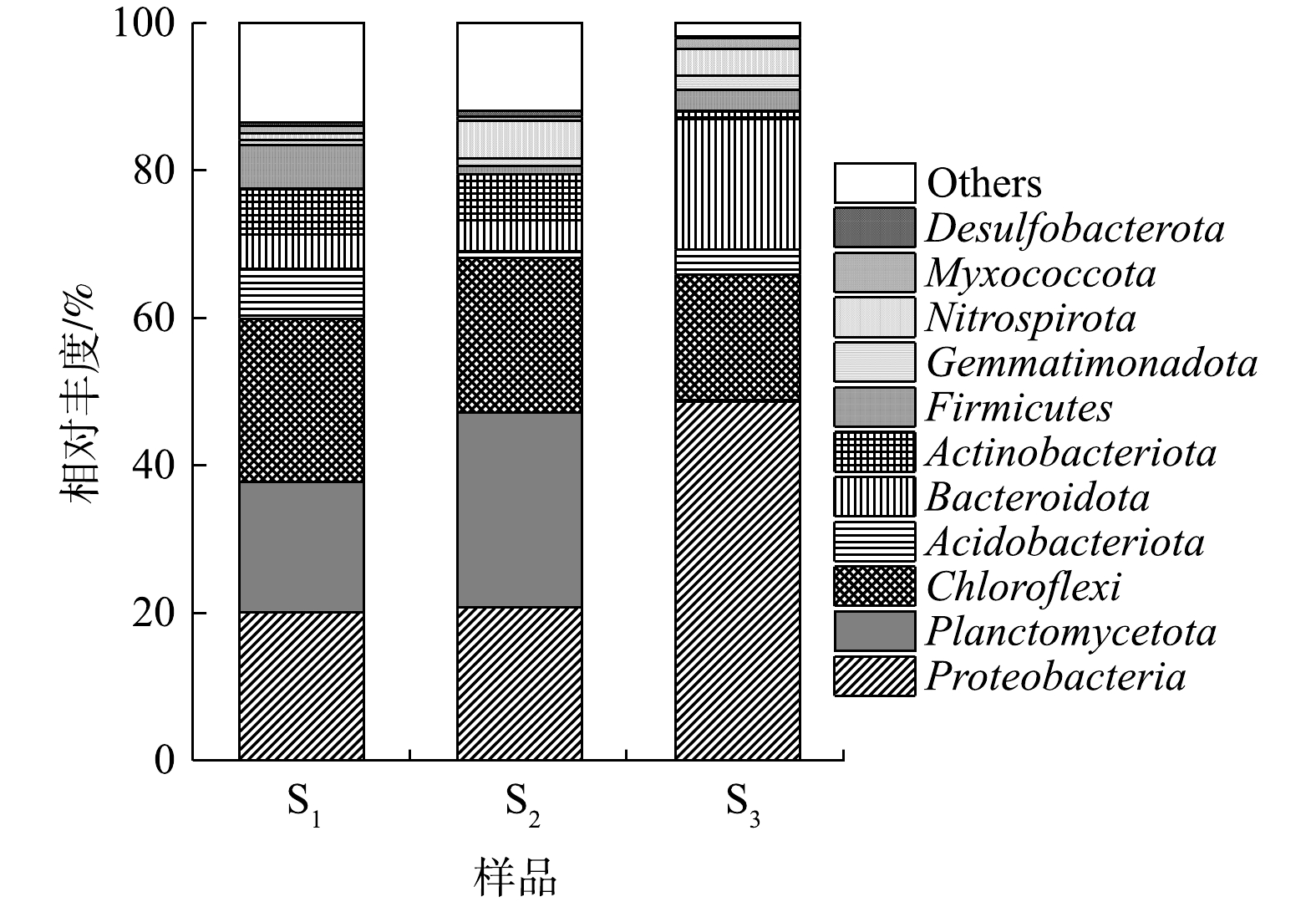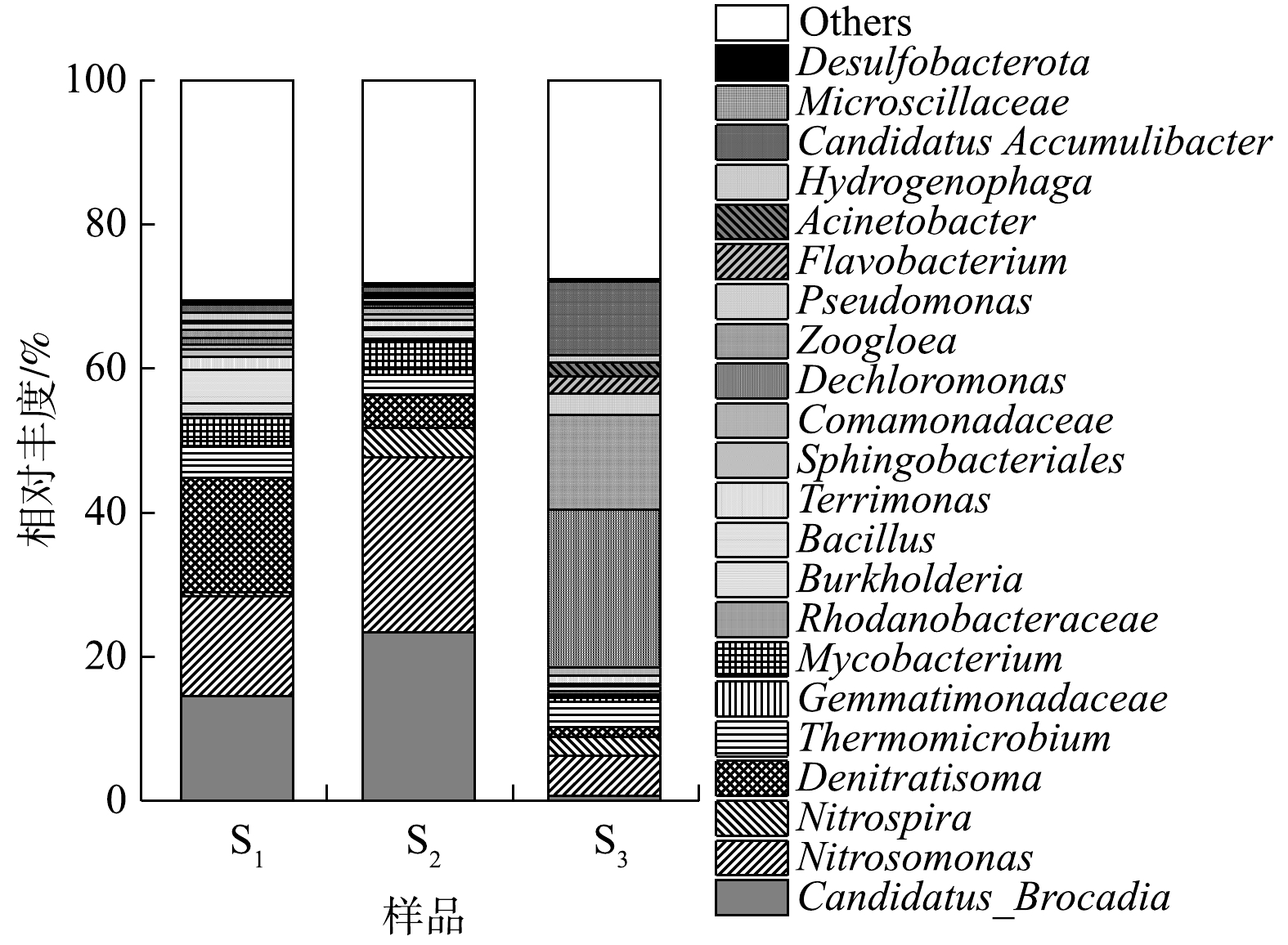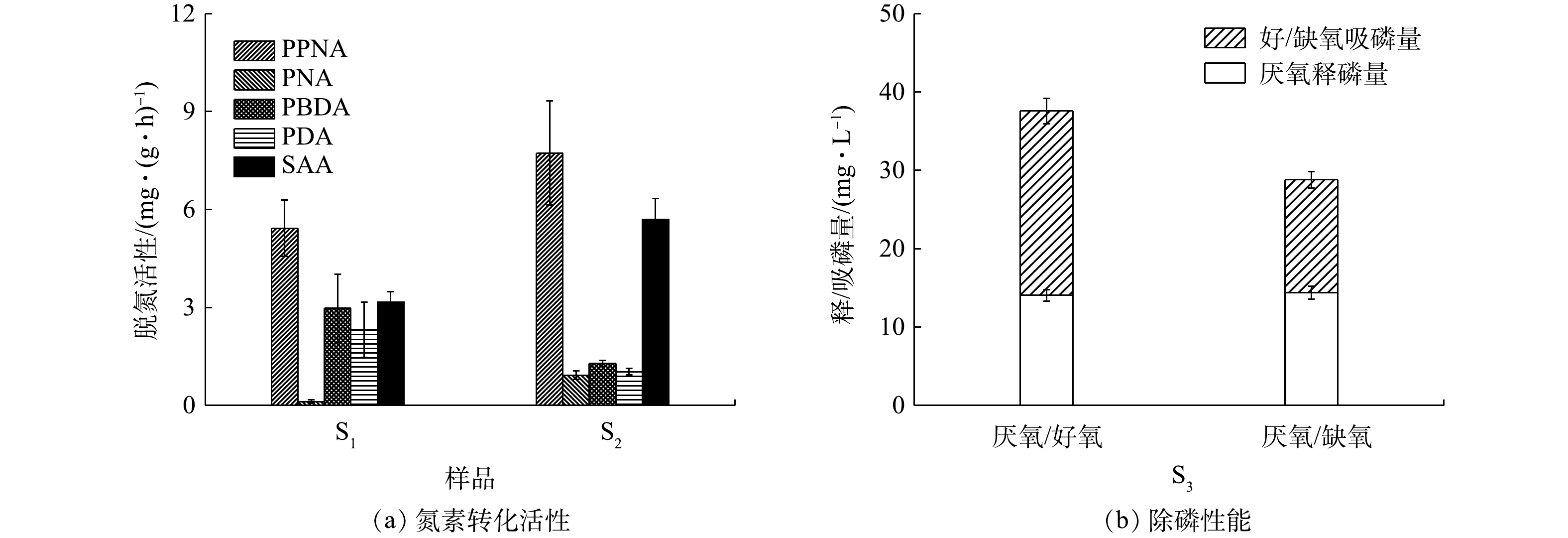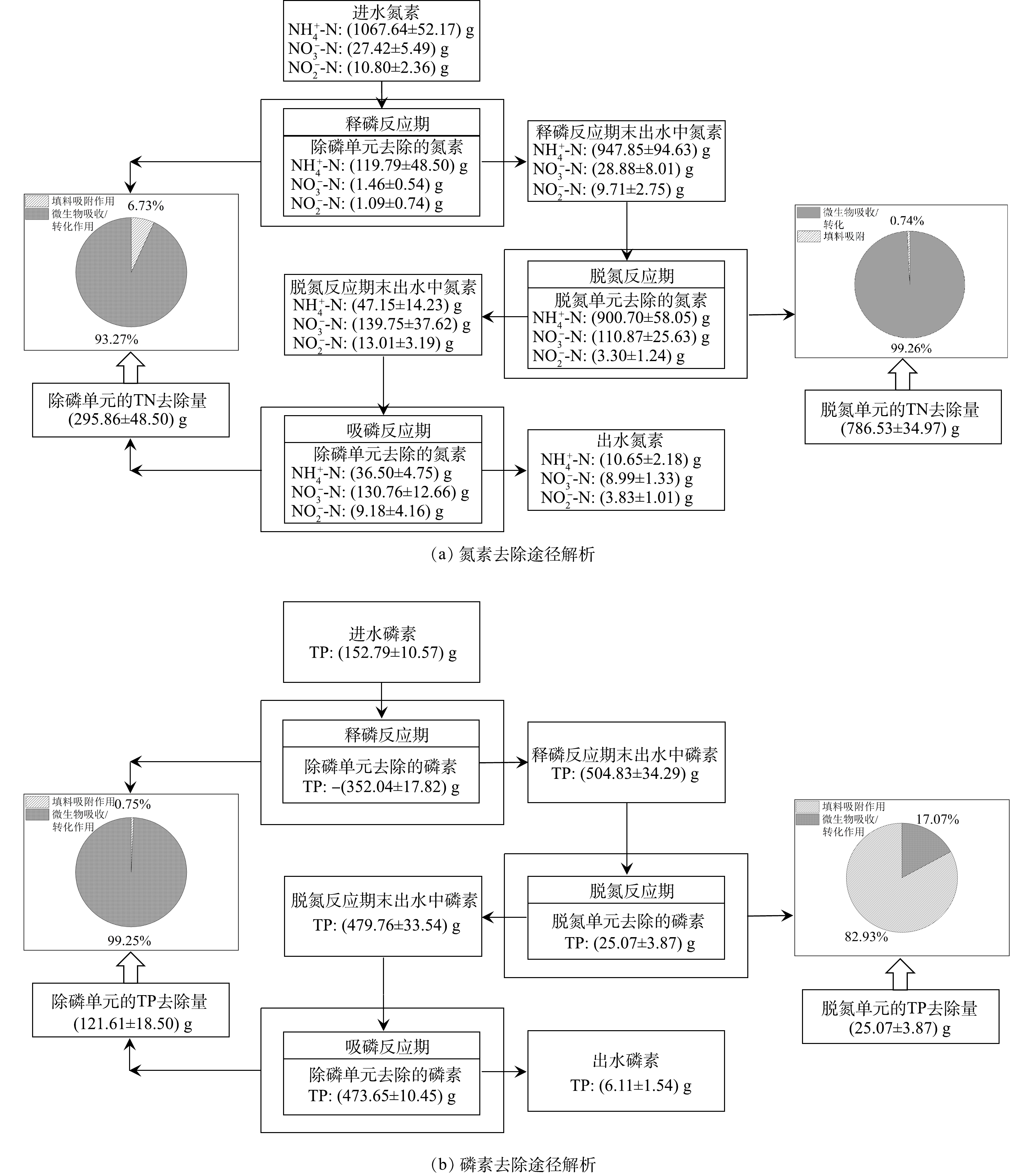-
据统计,2014—2019年全国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约1 900起,其中生态环境部直接调度指导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434起,水污染事件约占60%[1-2]。我国水系发达,当发生突发水环境事件时,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事发点下游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突发环境事件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因环境污染造成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突发环境事件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3]。因此,当遇到可能影响到下游饮用水源地的突发环境事件时,应急处置应格外谨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宁紧勿松,然而这样也会使事件应急处置难度提高、时间延长、经济代价增大。
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4]的109项水质项目中,分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集中式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和集中式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3类,分别有24项、5项和80项。若非集中式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的地表水体中发生突发环境事件,且涉及的污染物类别属于集中式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或特定项目,影响到集中式饮用水地表水源地水质的,则存在执行标准缺失的问题;同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个别指标严于同类型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或美国国家标准[5-7],如锑的浓度限制标准比WHO严格3倍,铊的浓度限制标准比美国严格4倍。
本研究遵循“饮用水源地安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地制宜、目标导向、严格控制”的原则,提出了在非集中式饮用水地表水源地执行的容许浓度要求及计算方法,适用于主体为河流及河流型湖库,理论上污染物类别包括所有在河流中不会发生自降解的物质。研究内容是对现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的补充,可为环境应急管理提供参考。
全文HTML
-
源强调查内容包括:1)流域内各段河流水体中特征污染物浓度采样监测;2)流域内各段河流水体中特征污染物本底值情况调查分析;3)流域各段河流河道底泥中特征污染物情况调查分析。在前述污染物源强调查分析基础上,核算出流域内各段河流特征污染物通量。
-
1)水域概化。将天然水域概化成顺直河道与稳态水流,将污染源概化成点源,利用合适的数学模型描述水质变化规律。
2)基础资料调查与评价。调查与评价各段水域水文资料(流速、流量、流向、水位等)和水域水质资料,收集污染物排放量与浓度资料、支流资料(支流数量、流量、流速与污染物浓度)等,并进行数据一致性分析,形成数据库。
3)控制点选择。根据水环境功能区划和水域内的水质敏感点位置分析,确定水质控制断面的位置和浓度控制标准。
4)水质模型建立。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建立水质模型。
5)容许浓度计算。应用设计水文条件和上下游水质限值条件进行水质模型计算,确定水域的水环境容量。充分考虑源头污染物通量、汇入支流污染物通量与河道底泥释放污染物通量等,在保证不影响下游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的情况下得出实际环境管理可用的特征污染物容许浓度。
1.1. 特征污染物源强和通量调查与分析的内容
1.2. 特征污染物容许浓度的计算步骤
-
以流域常规监测断面作为控制节点,将整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计算,将排入各河段的各种污染物作为输入条件,进行模拟演算。监测断面一定要反映环境敏感点的水质,且要保证出境水质达到下一水域的水质标准。
-
1)零维水质模型。零维水质模型,即污染物进入河道就假设其完全混合均匀(溶解或分散),且以此均匀体为整体分散(稀释作用),将污染物泄漏点至环境敏感受体间的河道作为一个整体,污染物在这一整体河道内均匀混合。该模型适用于持久性污染物,河流为恒定流,即流量稳定、水质均匀的河流状态,此时可不考虑污染物进入水体的混合距离。具体见式(1)。
式中:C0为污染物与河水混合均匀后的质量浓度,mg∙L−1;C1为上游来水中污染物质量浓度,mg∙L−1;Q为污染物泄漏点至下游某处区段内全部水量,L;q为污染物泄漏量,mg。
2)忽略弥散的一维稳态水质模型。忽略弥散的一维稳态水质模型,即一维稳态稀释、降解综合模式,忽略污染物的纵向弥散系数(在稳态条件下,纵向弥散系数对结果影响小)。该模型适用于非持久性污染物,河流为恒定流。当污染物在河流横向上达到完全混合后,分析污染物在纵向即水流方向输移、转化的变化情况时采用此模型。具体见式(2)
式中:C为下游某处污染物质量浓度,mg∙L−1;C0为污染物初始质量浓度,mg∙L−1;K为污染物的衰减速度常数,d−1;L为污染物泄漏点至下游某处河流长度,m;U为河流流速,m∙s−1。
3)一维动态混合模式。非持久性污染物、非恒定流采用一维动态混合模式。该模型适用于预测任何时刻的水质状况。具体见式(3)和式(4)。
式中:A为过水断面面积,m2;u为断面平均流速,m∙s−1;q为流量,m3∙s−1;d为纵向弥散系数,m2∙s−1;c为某污染物在x断面t时刻的质量浓度,mg∙m−3;s为各种源和漏的代数和。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c是一个空间与时间的函数。当已知边界浓度后(即泄漏点位置河道中污染物的浓度),可根据时间步长和空间步长一步一步向下求解,即可得到c值。
边界浓度(cbj)与污染物泄漏入河量M、泄漏时间t、河流流量Q等有关,其计算公式见式(5)。
式中:M为污染物泄漏入河的量,g;t为污染物泄漏时间,s;Q为泄漏点断面河道流量,m3∙s−1;cbj即为c在泄漏点的表征。随着污染物在河道中向下游推移,c是变化的。
以上3种计算数学模型为比较常见的污染物在水中的扩散模型。污染物扩散模型还有很多,比如二维、三维模型等,若是在基础数据及参数齐备的条件下,其预测的准确度会更高。但考虑到突发环境事件的特点,模型所需基础数据的收集比较困难;同时,应急处置应综合考虑最不利条件,有利于应急指挥与调度,因此,在应急处置阶段常常使用的是简单但危险性表征为最大的零维水质模型,即将特征污染物概化为保守物质或持久性污染物(如此设定可忽略特征污染物的自然衰减作用及河道其他物质对特征污染物的衰减作用,其危害性表征为最大),进入水体后视为完全均匀混合。
-
容许浓度计算数学模型(零维模型)见式(6)~式(9)。
式中:C为预测断面容许质量浓度,mg∙L−1;T为预测断面污染物通量,kg∙d−1;Q为预测断面流量,m3∙s−1;T总为流域污染物总通量,kg∙d−1;T支流为预测河段所有汇入支流污染物通量,kg∙d−1;T底泥为预测河段底泥释放污染物通量,kg∙d−1;Cn为各支流污染物质量浓度,mg∙L−1;Qn各支流流量,m3∙s−1;n为河流的支流数。
为满足更严格的水质要求,确保下游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环境安全,降低流域水环境风险,应以集中式饮用水地表水源地水质标准限值为基准,推导出上游各控制断面特征污染物最高容许浓度。同时,要求任一河段执行的容许浓度值不得直接导致其他相关河段特征污染物浓度超过其容许浓度值,当各河段特征污染物稳定低于容许浓度值后,可商请结束本次事件应急状态,解除应急响应。
2.1. 计算单元的选择
2.2. 计算模型的选择
2.2.1. 模型选择
2.2.2. 容许浓度计算数学模型(零维模型)的变换
-
以我国西部地区某尾矿库尾矿砂泄漏导致下游河流突发锑污染事件为例,分析了若执行本研究方法计算出的容许浓度时的经济社会效益。
2015年11月23日,我国西部地区某尾矿库因尾矿砂泄漏造成相关流域水体锑污染。该事件锑污染范围涉及A、B、C三省。在该事件的应急处置阶段,由于上游河流没有饮用水源地功能,而我国现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相应功能区划中未设置锑标准,故全流域只能参照“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标准限值”中的锑限值0.005 mg·L−1执行。而由于历史遗留原因及本次事件泄漏尾矿砂的影响,流域内有约100 km的河道因残存在河床上的尾矿砂中的锑与上覆水不断交换释放,使得各控制断面长时期处于轻度超标状态。为尽快全线达到0.005 mg·L−1的标准限值,解除应急响应状态,当地政府必须加大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控制,加上时处隆冬季节,低温及冰冻天气给现场应急工作造成了极大不便。
通过事后三省的环境应急监测数据分析并通过情景反演分析可知,若此次锑污染事件执行《WHO饮用水水质准则》(第4版,2011年)中关于锑的标准值0.020 mg·L−1,本次突发事件虽难以避免A与B两省省界断面超标,但可避免B和C两省省界断面超标,并可大大缩短应急响应时间。A省自启动应急响应至出省断面锑质量浓度降至0.020 mg·L−1,理论上可提前50 d解除应急响应;B省自A、B两省省界锑质量浓度超过0.020 mg·L−1至B、C两省省界锑质量浓度降至0.020 mg·L−1,理论上,B省可以提前49 d解除应急响应;C省自地表水中锑质量浓度开始超过0.020 mg·L−1至全线降至0.020 mg·L−1,理论上可以提前16 d解除应急响应。因此,若本次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执行对环境安全的WHO水质准则,与执行0.005 mg·L−1标准限值相比,本次事件理论上可提前16~50 d解除应急响应,三省均可减少一定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
通过事后统计得知,本次事件直接经济损失总计约6×107元。其中,A省约2×107元,包括管线引水工程、应急监测费用、筑坝拆坝费用、药剂投加费用、引流河槽开挖工程、山泉水引流工程、溢流井临时封堵和加固工程、尾砂/底泥清淤工程、涵洞口应急处置工程、行政费用等10项应急处置费用和财产损失;B省约1.6×107元,包括管线引水工程费用、车辆送水、筑坝拆坝工程费用、药剂投加、水利调蓄、应急监测、应急保障、行政费用等8项应急处置费用和财产损失;C省2.4×107元,包括管线引水、水厂除锑、水源安全、应急监测、车辆送水、行政费用等6项应急处置费用和财产损失。
通过情景反演分析,执行WHO水质准则限值的经济效益呈如下特点。
1)对A省直接经济支出的影响较大。应急监测费用和行政费用支出按照减少的应急响应天数(减少应急天数50 d)折算,应急监测费用减少约4.5×105元,行政费用支出减少约1.2×106元;应急投药工程按照投药量减少50%计算,支出费用减少约2.65×106元。因此,直接经济损失共减少约4.3×106元。
2)对B省直接经济支出有一定影响。应急监测费用和行政费用支出按照减少的应急响应天数(减少应急天数49 d)折算,应急监测费用减少约1.65×106元;行政费用支出减少约2.1×106元,故直接经济损失共减少约3.75×106元。
3)对C省的应急支出的影响。理论上C省除开展入境断面的地表水水质监测和水厂除锑工艺改造外,不需要开展管线引水、水源安全、应急监测、车辆送水等应急工程;由此可减少财产损失约1.5×105元,管线饮水工程费用减少约8.9×106万元,车辆送水工程费用减少约9×105元,应急水源保障工程费用减少约4.7×106元,应急监测费用减少约2.85×106元,应急行政费用减少约8×105元。因此,直接经济损失共减少约1.83×107元。
综上所述,如果此次事件中锑执行WHO水质准则限值0.02 mg·L−1,与执行0.005 mg·L−1标准限值相比,三省直接经济损失可减少约2.635×107元,约占实际直接经济损失(6×107元)的44%。若此次突发锑污染事件应急处置中饮用水源地上游各河段执行本研究提出的阶梯式容许浓度(浓度值0.005 0~0.120 0 mg·L−1),同样可大幅缩减应急处置时间并减少经济损失,而且此浓度范围能够保证下游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安全,并符合相应地区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
根据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亲历的多宗突发环境事件积累的经验,将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污染物标准嫁接到非饮用水源地会导致标准偏于严格,因而有必要制定基于水环境风险控制的应急处置阶段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以便最大限度地缩短应急处置时间,并降低应急处置成本。
当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若采用阶梯式容许浓度应对事件处置,可在大幅度缩减应急响应时间的基础上,减少应急投药量,缓解投加的药剂对河道水生生态的影响,缩短生态恢复时长,减少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更多地保障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同时,使用阶梯式容许浓度,可促使地方政府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充分考虑水环境承载能力,在保证产业发展前提下淘汰落后的生产工业装备和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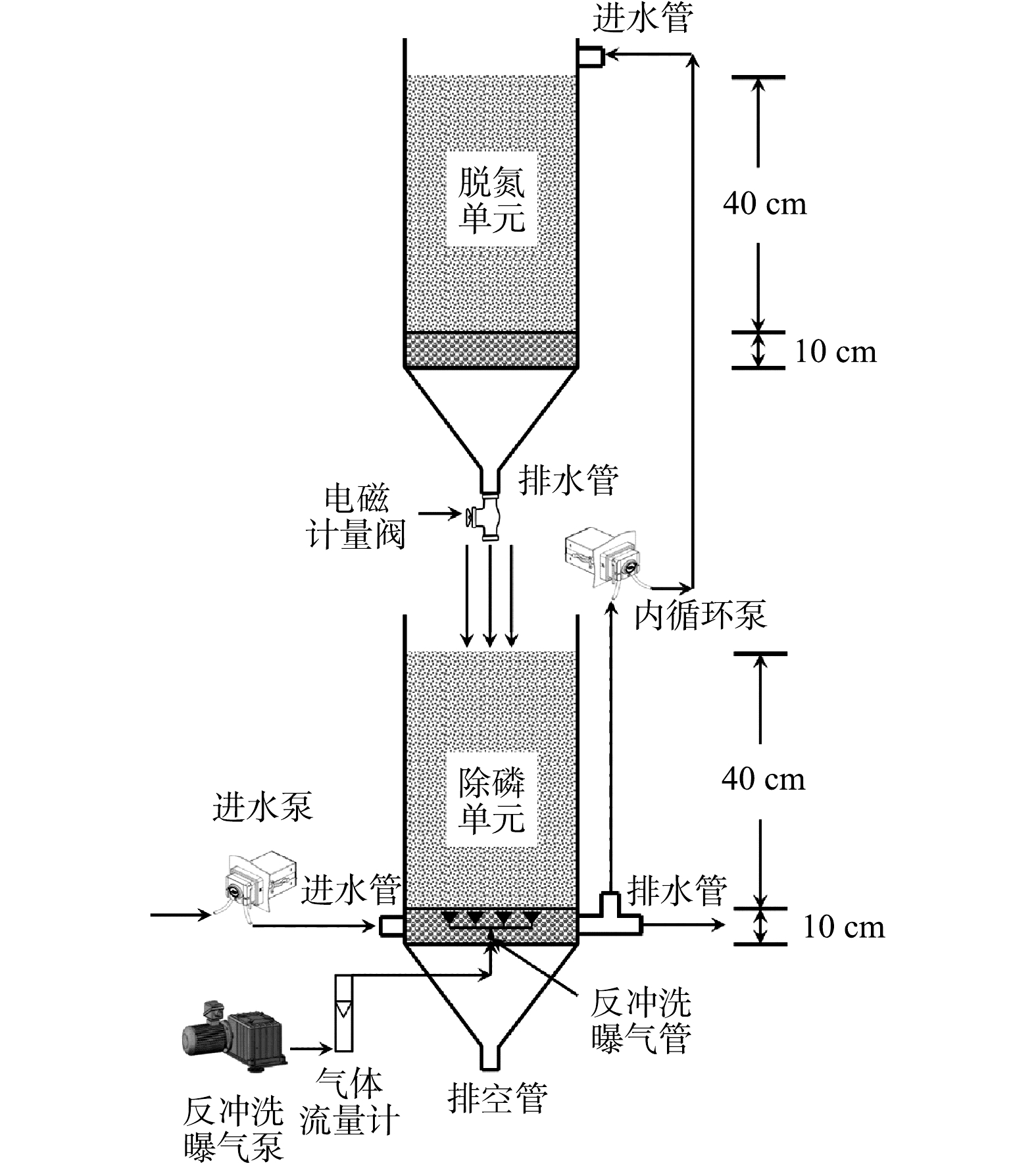
 下载:
下载: